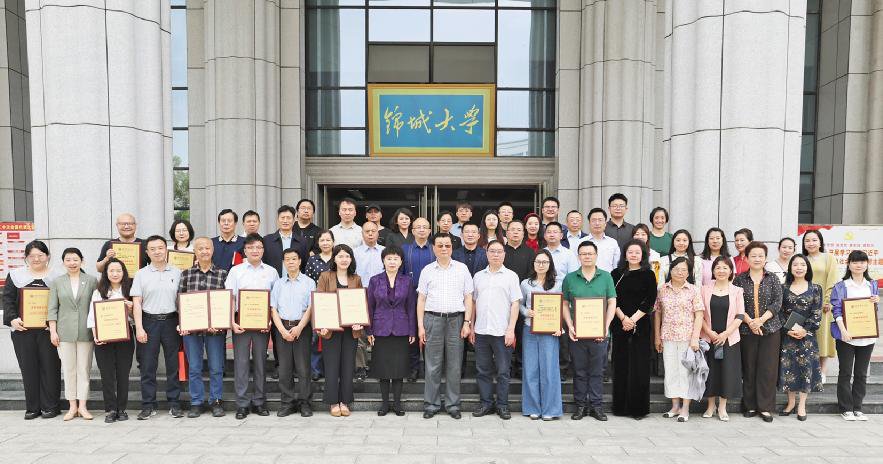光荣与梦想——写在中国美术学院创立九十周年之际
1
“书法,如果变成我的工作,那是再幸福不过。”戴家妙时常这样梦想。
这似乎是白日梦。那时,他是杭州一家著名妇产科医院的药剂师。炮制中药,是他的本职工作。整天捧着《 兰亭序》,在有的人眼里,那是“不务正业”。
那间堆满中药材、弥漫着药味的药库,被他当作“书房”。几个装药品的纸板箱,摆放整齐,就是书桌。稍得空闲,他铺好毛边纸,倒上墨汁,开始每日功课——临贴。
他无法做到心无旁骛。他要警惕是否有人来查看。突然,隐隐有脚步声传来。迅即收摊,迎接检查。但是,急促中撒在地上的墨水,暴露了刚才的一切。
“检查过了,我就摊开来继续练。”2018 年春天的一个下午,48 岁 的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副教授戴家妙,轻描淡写这段学书历程。那天,他刚刚给书法系的20 名 大一学生上完三个小时的楷书临摹课。
他在药库练字的日子有13 年,从18 岁 到31 岁。2001 年,是他人生的分水岭。这一年,中国美术学院在国内高校中首创书法系。系主任祝遂之教授看中了这个话不多,但勤勉、专注的书坛新秀。他被调去协助做筹建的行政工作。
“弃医从书”的戴家妙,从此开始他辛苦又幸福的日子。十多年来,从书法学硕士到书法学博士,从行政转到教学岗位,教学、科研、创作并行,他成了书法系书法理论教研室主任。
穿行在充盈着墨香的书法系教学楼走廊,你会“遇见”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 … 八位中国书法高等教育先驱者的照片挂在墙上。
先驱者的目光凝视着未来。就在另一侧的墙壁上,张贴着20 名 书法专业二年级本科生最近一次下乡考察的作品。晚学们正以这种方式向先贤汇报学业的进展情况。
今天,中国美院书法系有本科生110 人,硕士生、博士生60 多 人。今年秋季入学的书法与教育专业本科生,计划招20人,但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者超过750 人,创下历年之最。
55 年前,当中国美院的前身— — 浙江美术学院,在时任院长潘天寿的首倡下开设书法与篆刻专业本科教学时,只有两名学生:金鉴才和李文采。
如今桃李满天下的金鉴才先生,当年却不想学书法,一心想报考国画系的花鸟专业。他找到潘天寿先生诉说自己的想法。潘先生听完后,笑着说:“书法可不简单呢,不光要写好字,还要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要学的东西很多,你不要小看了。”
金鉴才当时不知道书法专业的创办背景:那是1962 年,潘天寿率中国书法家代表团赴日本交流,发现日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对书法教学很重视,书法学习风气之盛、书法家之多,令他惊讶。而在那时的中国,随着汉字简化和硬笔推广,传统书法却逐渐淡出中小学教学。
潘天寿忧心的是:中国的书法国粹,正在中国面临整体性的传承危机。
“日本人说中国已经没有书法了,今后学书法得去日本。因此周总理指示,要尽快培养出一批书法专业人才,与日本竞赛。”在《 首届书法专业教育追忆》 一文中,金鉴才这样记录潘先生对他说的话。
为往圣继绝学——这是潘天寿先生的梦想。可惜,书法教育于1966 年 中断了。1979 年 秋,美院重启书法教育,开始招收书法篆刻专业研究生。1 980 年1 月,陆维钊先生病逝前,仍坚持在病床前为研究生上了最后一课,并把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托付给了沙孟海先生。
“正是这样前赴后继,老一代书家挽救了上世纪我国书法人才所面临的断代之危,使我们能够看到当今书法的盛况。”首届研究生之一,后来主持书法系十年的祝遂之教授说。
盛况似乎有数字为证。中国有100 多 所高等院校开设了书法专业,有的学校一次就招100 多 人。各地的展览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即便是在书法这一传统文化领域,创新也成了流行的口号。
但祝遂之对盛况有冷静的思考。他批评书坛有浮躁急进之风。他援引沙孟海先生的话,希望年轻人“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字外的功夫,诸如文学、文字学、史学、哲学等学问修养,更要有崇高的人格修养…… ”
“真正把教育做得纯粹,真正能够培养出本专业的优秀人才。”5 年 前,祝遂之61 岁 时,仍发文表明自己念兹在兹的梦想。
2017 年 秋,当戴家妙在故乡温州举办首次个展时,祝遂之感言:“戴家妙精力集中,不为外部纷杂困扰,坚持自己的理想,气息醇正……”
这是戴家妙求学32 年 后对故乡的首次汇报。
汇报的题目是: 不 负初心。
2
18 岁 的刘海勇面临两个选择:他可以选择中文系,也可以选择美术系。
那是24 年 前,这位浙江乐清师范学校的优等生,和另一位同学一起,获得全校仅有的两个保送资格,入读温州师范学院的本科。
“读中文系吧,将来毕业了,可以做公务员,有机会当市长秘书。”关心他的人,这样告诉他。
但是,这个保送生的梦想,不是做一个官员,而是成为一名画家。他选择了美术系。四年后,他不出意外地成了乐清市一所中学的美术老师。
他仍然有梦。他决心考研。目标是中国美院国画系的研究生。
1999 年 9 月,刘海勇向学校请了一年假。对他来说,专业课不是最大的挑战,最难的是已放下七年的英文。他去杭州找著名的乐清籍英文老师万昌盛,寻求有没有学好英文的捷径。
一见面,万老师递给他一本书,书名叫《乐清之子》,里面记载的是,包括南怀瑾在内的20 个 杰出乐清人的事迹。这个情景,刘海勇终生难忘,“我一下子懂了”。
在中国美院附近的玉皇山,他租下一间阁楼。除了一张书桌和一张90 厘 米宽的床,再无容身的空间。每晚和成群的蚊子作战,从仲春直到中秋。洗澡和如厕,排着队匆匆解决。东北来的考友说,吃生大蒜可增强记忆力。他就照办,虽然辣得泪水汨汨,但仍坚持,希望多记住几个英文单词。
第一年考试结果,专业分过了,但英文成绩离录取线差6 分。
刘海勇不甘心。他要继续圆他的梦。但他不能再请一年的假。于是,在杭州和乐清之间,他开始周而复始的奔波:周三下午上完课,坐汽车去温州,乘一夜的火车,第二天凌晨到杭州,赶到浙大去听英语课。周日晚上,又是一夜的火车,赶回去上班。
在夜行火车上,他背诵着英文,也背诵着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2001 年,刘海勇终于如愿,师从中国美院国画系徐家昌教授。三年后,他毕业留校任教。接着,他又考上中央美院的博士研究生,师从张立辰教授。巧的是,张立辰和徐家昌,均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浙江美院,同为潘天寿的弟子。
“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故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五十多年前,20 来 岁的张立辰和徐家昌,亲耳聆听了潘天寿先生这样的论述。
“坚持以国族之画传承光大民族心志,坚守中国文化本位与民族特色。”这是潘天寿一生的梦想。
“这也是我们代代传承的梦想。”42 岁 的刘海勇这样说。如今,刘海勇已是中国美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画系副主任,分管本科生的教学工作。
“处处为学生着想,既条分缕析,又能掰开揉碎,既口传精义,又能上手示范。”尉晓榕教授,这位中国美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院长,如是评价刘海勇。他还认为,刘海勇“凭着沉潜和奉献两种精神,和艺理双修的轨制,为同门做了一个榜样”。
对艺术后学,刘海勇要求自己象前辈一样,做到“真诚相待、谆谆教导、倾囊相授”。他摸索着自己的教学经验。2015 年,是刘海勇留校任教的第11 年。这一年的4 月,中国美术学院和浙江省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了《刘海勇‘ 境.十年’ 中国画教学与创作汇报展》。
“让我们一起去找一找先辈的光荣!”当有人在课堂上左手画笔,右手手机,忙着刷微信时,刘海勇忍不住提醒:潘天寿先生,37 岁 前就已编就《中国绘画史》和《中国书法史》;黄宾虹先生,42 岁 写就《宾虹论画》。
“海勇,你看现在年轻人的画都是‘ 淡淡的’,这是为什么?”在一次国画系毕业生作品展上,许江,这位中国美院的“当家人”,在看展览时突然发问。
这个问题引发了他的思考。他发现,年轻学子的作品,最大的问题是,笔墨精神内涵的浅薄化与小情趣化,缺少对中华文化精神、民族精神的彰显。
他在《美术报》撰文发问:在艺术院校大扩招的背景下,在越来越多的艺术学子缺少社会生活历练的情况下,如何让他们发掘当下安逸情趣表象背后的深层生活感受?如何在笔墨中融入真切的人文关怀、人文精神?
他的答案是,技法传授固然重要,艺术创造与社会实践,与生活更要紧密结合;传承中国文化优秀传统中的写意精神,并进行当代拓展,是一个紧迫的课题。
他告诉学生,“种瓜得瓜”,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在迎接中国美院九十周年校庆到来的日子里,他想着要画什么。他想起了勤劳、善良的外婆,想起了金秋时节,外婆家挂满瓜果的庭院。于是,他挥毫泼墨。
他给这幅作品取名:种瓜得瓜。
3
有一位诗人说,管怀宾,是一个用材料写诗的诗人。钢材、山石、混凝土、不锈钢、玻璃、瓶胆、木门、草、陶器… … 管怀宾,这位中国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院长,用这些生命中随处可见的东西,创作一件件令人或迷惑不解,或陷入沉思,或惊心动魄的作品。
今天,作为一名有影响力的装置艺术家,人们难以理解,他本来的专业是最传统的中国画。1985 年 至1989 年,他在西子湖畔完成国画系的四年学习。
这位国画专业的学生,如饥似渴地阅读图书馆里那些刚刚传播到中国的西方现当代艺术及其思想新论。他的艺术观念被悄悄地刷新。
“梦想的种子就在那时播下。”管怀宾告诉来访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学校省下一笔本用于购买大巴的钱,改为购买国外的书籍。他赞叹这是多么大胆且英明的决定。他把这些书籍视为他的艺术观念的源头。
不过,他对学院购书一事的描述可能有误。更权威的记载出现在许江《学院的力量》一文中:“难忘1979 年,学院党委集中全年经费的10%,购买了9 万 元的国外美术图书资料,并以展览的形式,一日一页,历时月余,吸引着在校和全国的艺术青年”。
“这不仅一举改变了学院图书匮乏的状况,而且以一种开放的胆魄,将当年的艺术教学蓦然置入国际艺术视野之中,置入中西文化互动激荡的格局之中,并由此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学子,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进程。”许江写道。
1993 年,受到“深刻影响”的管怀宾和妻子一起,东渡扶桑,在那里开始从传统绘画转向现代艺术的创作实践。在日本,他完成了一系列装置作品,参与过不少国际性重要展览。
10 年 后,当管怀宾在日本转型成为一名具有独特风格的装置艺术家时,许江提倡的“和而不同”理念 ,吸引着一批当代艺术领域的前卫艺术家们加盟中国美院。
回来吧!远方的游子。中国美院向管怀宾发出了邀请。2004 年 春天,管怀宾回到魂牵梦萦的母校。在获得东京艺术大学博士学位后的第三天,他站在阔别15 年 的母校课堂上,讲述他对当代艺术的理解。
他的梦想是,在中国开辟新的跨媒体艺术天地。2010 年,中国美院成立跨媒体艺术学院,他任分管教学的副院长。两年前,任院长。如今,这所年轻的学院已下设3 个 系、5 个 研究所,拥有185 名 本科生,54 名 硕士、博士生。
今天,作为中国重要的装置艺术家之一,管怀宾被艺术界认为“善于将传统文化元素和感知方式,解构并溶入到自身的语言系统和作品构架之中”;他“将中国古典造园美学融入其空间装置形态,使传统文化元素在当代艺术语境中获得广泛的延伸与拓展”。
有人问他,你今天从事的装置艺术,是西方的舶来品,这和你当年从事的国画专业,似乎有点遥远。他的回答是:其实没有距离,艺术是相通的。
管怀宾的答案,令人想到90 年 前林风眠先生的追求。1928 年,当28 岁 的林风眠赴任这所中国最早创立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时,心怀的梦想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
90 年 后,这四句话被印在一扇两米多高的门框四周,竖在中国美院南山路校区的草坪中央。
是的,林风眠的继承者们,并没有忘记先贤的梦想。
4
余旭鸿26 岁 那年,访问了欧洲60 多 个城市的上百家美术馆或博物馆。
那是2002 年 6 至 9 月,他正在读中国美院油画系的研究生。他没想到,十多年后,自己成了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的执行馆长。
“这次欧洲游历,让我对蔡元培先生的美育思想,有更深切的体悟。”在2018 年 的春日里,余旭鸿一边引导访客参观,一边这样回忆。
他刚刚策划了中国美院九十年师生捐赠作品展。这次展览取名为《世纪同心》。美术馆外面的橱窗里张贴着林风眠生前题写的《永保青春》,还有吴冠中生前题赠的《母校万岁》。
此刻,当你置身美术馆,站在林风眠、潘天寿、黄宾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