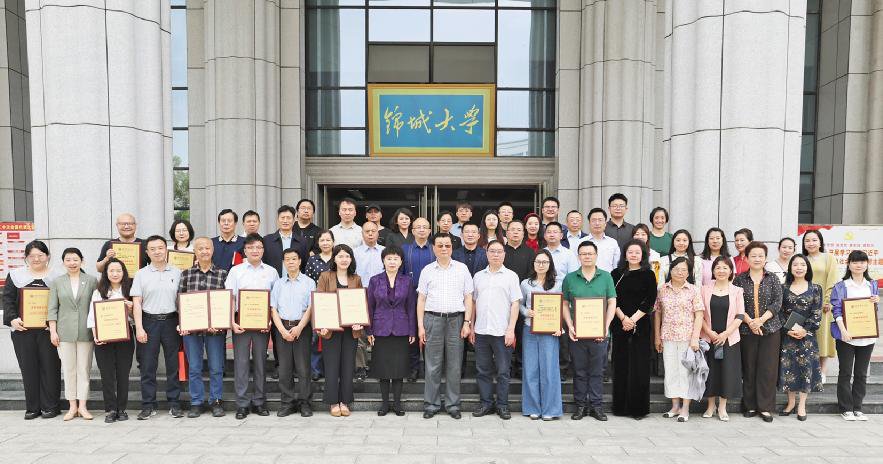先锋派对传统的背离与回归听陈晓明先生《先锋派与传统性》讲座所感
先锋派是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鲜活存在。对于先锋派,文学界一直强调其先锋性与先锋经验,但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教授在题为 《先锋派与传统性——当代小说艺术的潜在流变》的讲座中却以独特的眼光发现了自1980年代以来先锋派对传统的背离与回归。
一、“变革”从何而来传统的中国文学主要有两脉:第一脉是以《史记》为宗的史传传统,在这一传统下,成就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第二脉是戏剧、诗词之脉,成就了如《红楼梦》这样的文学经典。这两脉文学传统在中国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五四白话文运动打破了中国文言文的文学传统,西化并重塑了中国的语言系统,把西方文学(世界文学)大力引进,催生了五四新文学。在当时,这不仅是文学界的变革要求,也是时代的要求。然而,这也是传统与现代的深刻裂变。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也常常给中国文学界带来强烈震动,由此有了文学的代际问题,如 “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文学。现在的“90后”们,有多少人还能静下心来完完整整地读完 《红楼梦》?不过百年,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审美经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然而,在西方却并非如此,西方文学,尤其是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表现出一种超时间的性质。“西方浪漫主义的诗学,追求的是文学的绝对性,文学为上帝给予的,它具有神本体。”(陈晓明语)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把整个西方传统,列为莎士比亚的传统。即所有的后世作家,只有和莎士比亚决斗,他(她)才是伟大的作家。只有战胜莎士比亚,或者能够和莎士比亚对话,才能够称得上伟大。西方文学,如获诺贝尔奖的莫迪亚诺《暗店街》,在法国,8岁的孩子也读,80岁的老人也可以读。文学的审美经验、心理结构并不像中国那样有代际性。
因而陈晓明先生说,“中国文学的变革,总是要通过过去来实现。因为过去的文学本身没有依据,它在变革中寻找过渡性、替代性、暂时性的方案,所以我们的文学,总是处在一种变革的焦虑中,我们应当看到文学变革的实质与精神。因而在讨论先锋派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文学史的实质,看到当代文学发展的内在精神。在这样一个变革当中,我讲到了一个传统性的问题。我说的传统性,不是先锋派的产生、形成过程中的传统性,或者说是先锋派内含的传统性,与此相反,我要说的是,在先锋派的先锋性之中,我们也能够读出传统性。”
二、激进性与传统性任何变革都是对于传统的创新。先锋派呈现出很大的断裂性,但先锋派并非铁板一块,孤立于中国当代文学中。陈晓明先生引入了先锋派与传统性的视角,在先锋派的先锋性中读出了传统性。这种传统性在1980年代中国文坛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强烈冲击时,曾经被打破,被搁置,如刘索拉、徐星、马原、莫言的小说。但是当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魔幻主义传入中国后,文学界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被视作本土经验的乡村,也可以是先锋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一开始就既是现代主义,又是传统主义,由此形成了拉美后现代主义,一开始便呈现出与传统调和的姿态。本土乡村经验,构成了先锋与传统的内在关联。
1980年代的先锋派呈现出一种鲜明的主观化、抒情性、后悲剧的风格。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里,余占鳌在去杀死与母亲通奸的和尚之前,先到了父亲荒芜的墓地,那墓在梨园深处,满树雪白的梨花盛开着。当余占鳌从和尚的肋下拔出剑来时:“梨树上蓄积的大量雨水终于承受不住,扑簌簌落下,打在沙地上,几十片梨花瓣儿飘飘落地。梨树深处起了一阵清冷的小旋风,他记得那时他闻到了梨花的幽香……”
这是一段主观性极强的叙事,甚至不乏意识流的启发 (中国的意识流以王蒙先生为先驱)。试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杀死了与母亲通奸的和尚,本来是一件极其惨烈的事情,但是莫言没有写和尚的鲜血横流,表情扭曲的惨态,却将笔落在了“梨花的幽香”上。这种意境、笔法,正是古典美感的一种,不是怨愤与狂怒,而是人生的哀戚。再如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妻妾成群》等作品中亦不乏这样的例子。然而,仅仅依靠着主观化、抒情性和后悲剧的先锋文学却没有走多远,这既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也是因为缺乏足够的思想底蕴。
到了1990年代初,经过短暂的沉寂,先锋派的作品随之有了更广泛的传播。一方面,是因为邓小平南巡讲话,思想界比前二年更加开放;另一方面,先锋们着手写作长篇小说,其先锋派的形式主义实验性有所收敛。传统性开始以一种“复活”与“幽灵化”的姿态呈现。比如,贾平凹的《废都》“后记”中写道:“……中国的 《西厢记》《红楼梦》,读它的时候,哪里会觉得他是作家的杜撰呢。恍惚如所经历,如在梦境。好的文章,囫囵囵是一脉山,山不需要雕琢,也不需要机巧地在这儿让长一株白桦,那儿又该栽一棵兰草的。这种觉悟使我陷于了尴尬,我看不起了我以前的作品,也失却了对世上很多作品的敬畏,虽然清清楚楚这样的文章究竟还是人用笔写出来的,但为什么天下有了这样的文章而我却不能呢?”在1990年代的小说里,大量关于家族,关于20世纪的中国乡土叙事不胫而走,它构成了当代小说最为成熟老道的一脉,也在这方面形成了中国文学独有的现象。因而,在传统这一层面上,乡土叙事个性化内化,同时又带有先锋派的激进性。如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阎连科的《受活》《四书》,贾平凹的《秦腔》《古都》《黑灯》,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一句顶一万句》。先锋性中的传统性正是先锋派在历史错动中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它带给文学写作、文学创新以无边的可能。
(田晓雨,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