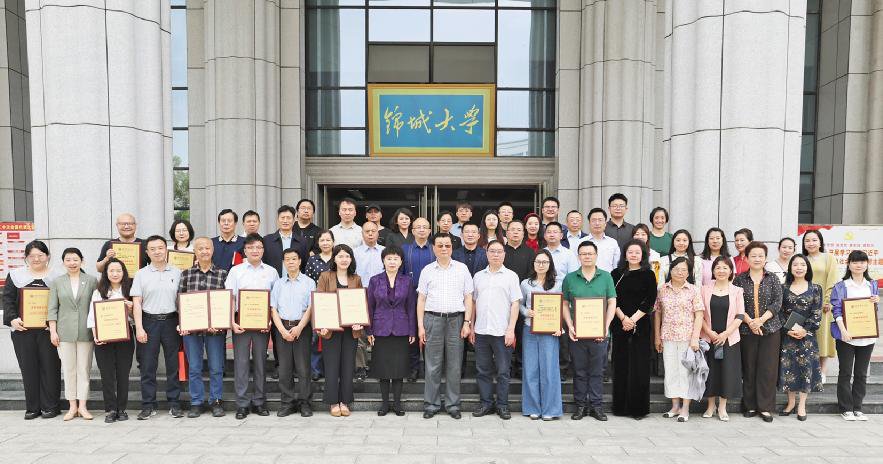庄维石先生二三事
步入大学,是人生的航船确立目标、锁定航向的关键阶段。上一所称心的学校,学一个喜爱的专业,是一生的幸运。若在大学里,能遇到一批博学高才、治学严谨的老师,那就不仅是幸运,而且是幸福了。我走进山师,就收获了这种幸运和幸福。
1959年我进山师后,不仅越来越喜欢这座举“市”无双的美丽校园,而且对所学专业,越来越喜爱,对授课的教师,越来越崇拜。当年,系里给我们配备了很多优秀教师,像田仲济、严薇青等先生,都是全国知名的学者。一些中青年教师,也都身正学高,造诣颇深。在众多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教学有方的老师里,庄维石先生是我最景仰的老师之一。
庄老师给我们讲授古典文学的先秦部分。他当时年已半百,穿着朴素,谈吐文雅,待人谦和,举手投足都散发着儒雅的学者气质。上庄老师的课,就是一种享受。遥远的诗经和诸子散文,他都烂熟于心,讲析起来,条分缕析,胸有成竹,滔滔不绝,从不看讲稿。他对各家观点,了如指掌,无论介绍哪种说法,他总是信手拈来,先援引原文,再加以评述。每当亮明自己的见解时,他旁征博引,博采众长,有些则是他的独家之说。他只要引述别家观点,总要说明出处,他竟连出处的章节页码都说得一清二楚,准确无误。学子们无不佩服庄老师学问深厚,记忆力超群。庄老师一上课,总能一下子就把学子们吸引住。他声音总是那么洪亮,有磁性;精神总是那么饱满,有激情;内容总是那么丰厚,有趣味;教态总是那么从容,有大家之风。他能牵引着学子们的思路,与他讲课的语流同步,他能调动学子们的情绪,同他发抒的感情共鸣。多会儿上庄老师的课,我总是听着入迷,沉醉其中。
庄老师教学严谨,对学生也要求严格。记得他给我们讲完庄子的《逍遥游》后,要求我们背诵全篇,并利用晚上辅导答疑时间进行抽查。说实话,这篇散文篇幅较长,难驾驭,背诵有难度。当课代表宣布抽查名单时,我们紧张得大气儿不敢出,都害怕抽到自己,结果我“不幸”单上有名。苦苦背了一下午,就是背不熟,无奈时间已到,只好硬着头皮面见老师。庄老师按名单开始让逐个背诵。结果上阵的同学,个个都和我差不多,开口:“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就开始的两句,背得还像样,以后就越来越结巴,再后,即使老师提示,也背不下去了。还没轮到我,庄老师便脸色凝重地问:“有没有全背过的?”教研室里鸦雀无声,一个应答的也没有。显然,庄老师很失望。他摇摇头,叹了口气,终止了背诵。他对我们说,你们年轻轻的,记忆力正好,看来是没下功夫呀!这可不行,学中文,就得大量背诵诗文,这是基本功啊!要不,将来怎么教学生?于是,他向我们介绍了他自幼背诵的经验,并给我们示范,背诵了《逍遥游》全篇。我们听老师背得滚瓜烂熟,一气呵成,连个哏都不打,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面对饱读诗文功底深厚的老师,我们望尘莫及,羞愧难当。
1978年,我调到中文系任教后,又特意去聆听了庄老师的课,正逢他讲屈原的《离骚》。虽已是年近古稀之人,但他讲课,仍然精神矍铄,声情并茂,风采依旧。
有一次,在我住的筒子楼走廊里,看见庄老师招呼我儿子,非常亲昵地送给我儿子一沓香烟盒纸(当时香烟盒纸是小孩最喜欢的收藏品,折叠起来,当流行玩具)。我这才知道,原来庄老师和我同住一个楼,是邻居。于是,我就去拜访老师。他住在一间14平方的北屋里,终日不见阳光,室内,陈设简陋,家具破旧,满屋凌乱。当时师母已过世,只有小儿子陪伴,显然,父子二人过得很清苦。见此境遇,我心里很不是味儿,可庄老师谈笑风生,好像一点也不在意。以后每次去拜访,他都是坐在那把旧藤椅上看书,见我去,他便兴致勃勃地与我聊天。庄老师一向健谈,每次都从他的谈吐里,获得很多知识和教益。
那年过春节,我将我们家的传统酥菜和各种蒸包,送给庄老师品尝。就这么一件小事,竟让庄老师久久铭记,他搬到教授楼后,每次我去看望他,他总要提及此事,一再感谢,谢得我满脸羞红,很不好意思的。一个满腹诗书的大学问家,对如此区区小事,念念不忘,其重情重义的品德和情怀,怎能不让人感触、感念、感动!
大家都知道,在“反右”和“文革”期间,庄老师屡受冲击,但是,无论是在逆境中,还是在困境中,他坚守信念的初心始终不改,他“学而不厌”的痴心始终不改,他“诲人不倦”的诚心始终不改,足见庄老师境界高远,心胸开阔,气度非凡。所以,我由衷地敬仰和怀念“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庄维石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