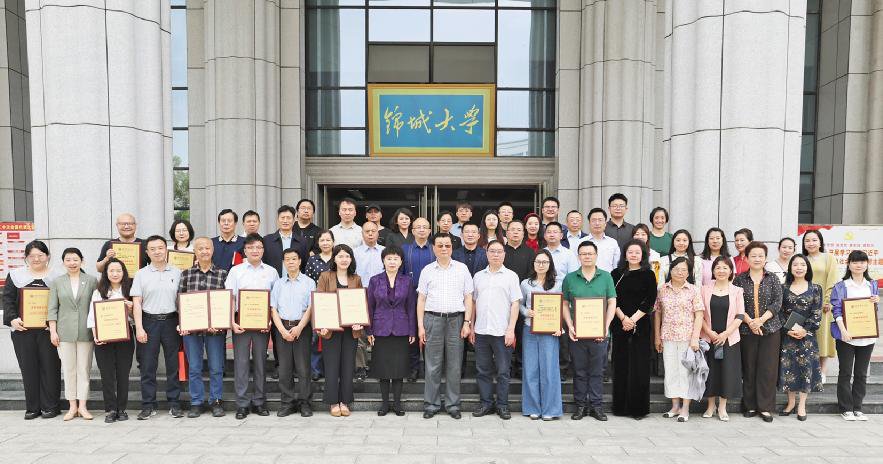解读中国传统“生生”美学
2017年11月7日,由《光明日报》主办的品牌栏目“光明讲坛”首次走进山东大学。曾繁仁教授应邀为山大师生带来了题为“跨文化研究视野中的中国生态美学——从比较视野解读中国传统‘生生’美学”的学术讲座。
曾繁仁,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国家重点学科山东大学文艺学学科学术带头人,著名美学家,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奠基人。
现今国际上活跃的生态美学流派主要有两个:一是欧陆现象学,二是英美分析哲学环境美学。中国学者一直以来都在思考:中国是否存在生态美学?如果存在,中国的生态美学又是什么?当今它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为了尝试解答这些问题,曾繁仁教授通过跨文化的研究方式,探索中国生态美学在传统文化中的体现及其前进方向。
一、跨文化研究的提出及其对生态美学研究的影响
跨文化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提出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路径针对由西方中心论派生出的法国学派“影响说”和美国学派“平行说”,倡导文化多元共生与跨文化比较对话。“影响说”旨在探寻各种文学形态的影响关系,比如说模仿、继承等;“平行说”则是探寻文学形态的内在规律。然而不论是“影响说”还是“平行说”,本质上都是倡导西方中心论。
跨文化研究的出发点主要是基于世界文化发展“类型说”代替占据统治地位的“线型说”。“线型说”主张文化发展是线型的、是由生产水平决定的。西方的发展早于中国,生产水平高于中国;中国古代几乎没有提到过美的概念,也没有成形的美学体系。因此,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全盘西化、“以西释中”。“类型说”则主张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样式和类型。中国过去长期经历的农业社会,是一种传统的自然友好型生态社会;古代希腊以商业与航海为主,遵循的是战胜自然的文化模式,这两种文化应是共生、互补的。同时,跨文化研究的提出也具有特殊的语境,即中国处于经济振兴、中华文化复兴之时。一个民族的复兴,只有经济的强大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复兴和文化自信,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推动民族的发展和前进。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中国学者探索跨文化研究“类型说”,以发展中国的生态美学学说。
生态美学是20世纪兴起的一种美学形态。在西方,它包括欧陆现象学生态美学和英美分析哲学环境美学。中国的生态美学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引进、介绍西方环境美学为开端。21世纪初期,中国学者逐步开始独立的生态美学研究,致力于揭示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中的生态审美智慧的现代意义,以此开始与西方环境美学的对话,进入跨文化研究阶段。生态美学以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等为其重要理论支撑,反对人类中心论,提倡生态整体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及人与自然亲和、共生的审美关系,将自然视为人类的家园。“人类中心论”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产物,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而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中心论必然会被淘汰。我们应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达到人类和自然的共生,这也是我们之所以采取跨文化研究路径的原因。
二、中西生态美学跨文化对话之成因
中西方之所以在生态美学领域能够达成跨文化对话,主要是因为两者之间既具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所谓共同性,就是说双方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这才使跨文化对话具有可能性。共同性有二:一是生态问题是中西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自1972年第一次国际环保大会——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西方将生态环境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而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与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二是中西方生态美学都具有某种反思性与融合性,即对于传统工业革命的人类中心论的反思与超越,并且倡导人与自然的融合性。
在生态美学领域中西方也存在差异性。差异性使得跨文化对话具有足够的空间,也使得中国生态美学得以发展:
其一,近十多年来中西方存在着“生态”与“环境”之辩。西方特别是英美学界力倡环境美学,而对于“生态”一词颇有微词;中国学者则主张生态美学。从字义上讲,“环境”(environment)有“包围”之义,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对立;而“生态”(ecology)则有“家庭、经济”之意,是对于主客二分的解构,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从内涵上说,“环境”一词具有人类中心论的内涵,而“生态”则抱持生态整体论;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生态”一词更加切合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和“天人合一”的审美智慧,而环境美学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相接轨。“环境”一词,有将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排除在外之嫌。
其二,从生态文化的发生来说,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强调“天人合一”,因而生态文化是一种由既定因素决定的相对稳定的原生性文化,或者叫“族群原初性文化”,是一种在原始形态的农耕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人与自然共生、亲和的文化形态。而西方20世纪初期所产生的生态文化是一种反思的后生性文化,是对于工业革命破坏自然之后果反思的产物,两者有根本性的不同。中国古代哲学以天人相和为其文化模式,中国的审美与文学艺术崇尚“道法自然”,诗辞歌赋、音乐书画、园林建筑等,都主要以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为对象,融注了非常浓郁的生态意识。西方古代文化则是一种科技文化,贯穿着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且西方生态文化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传统文化的启发。如海德格尔根据自己对老子的“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的独特体悟,提出了“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梭罗出于对孔子“仁爱”的向往,提出了“人与自然为友”的主张,在他自己的著作《瓦尔登湖》中引用了《论语》里的“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
其三,从生态美学的话语来说,中西方生态美学也有很大的差异。需要说明的是,审美是人的一种特定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是人与审美对象之间的肯定性情感经验。人类审美的情感经验有共通性,又有民族的差异性。西方人主张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是感性认识的完善等,中国人则称“生生之为美”。在生态美学上,中西方各民族之间都有自己特殊的话语。西方欧陆现象学生态美学主要使用“此在与存在”的“阐释学”方法与话语,英美分析美学之环境美学则主要使用科学的“分析”方法与话语,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对象模式、景观模式与环境模式等的恰当性进行科学分析,最后导向对于环境模式的肯定。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生态审美智慧,是以“生生”为核心的古典形态的特殊话语。《周易》中有“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生生”,即“生命的创生”,使万物获得旺盛的生命。“生生”与“生态”具有内在的相融性,“生生之谓易”的文化传统目前仍然有其生命力,可以充实到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与生态美学理论当中去。
中国传统的“生生”之学,体现了一种东方文化特有的“有机性”与创新性内涵,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整体性与关系性的文化行为,既不同于英美环境美学“分析”之科学性,也有别于欧陆现象学美学“阐释”之解构性与主体性。由此,西方之“阐释”“分析”与中国之“生生”就构成一种跨文化的对话关系。
三、中国古代“生生”美学的特点
“生生”美学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具有明显区别于西方美学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
第一,“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生生”美学的文化背景。“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具有根本性的文化传统,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中国人观察、思考问题特有的立场和视角,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古代各种文化艺术形态的产生发展与基本面貌。“天人合一”观念最早来源于原始宗教“神人合一”,发展为《老子》的“道法自然”、《周易》的“与天地合其德”等观念;汉代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学说,提出了“天人感应”一说;直到宋代张载正式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这一思想演变的过程,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当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和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的审美关系的追求。这种天人和谐的观念,使中国美学、艺术始终追求一种独特的、东方式宏观的中和之美,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物质的微观的和谐之美迥异其趣。
第二,阴阳相生的古典生命美学——“生生”美学之基本内涵。甲骨文的“生”字,就像草从地上长出来的样子,意味着万物繁育。“生生”的关键环节是“气”。《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周易》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由此说明气乃生命与万物之本,阴阳之气交感诞育万物生命成为宇宙人生之规律。《周易·系辞上》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之道贯穿天地万物的创生、生长、发育之始终,成为生命的根源,也成为艺术创作的根本规律,这是古代中国特有的美学智慧。书法的黑白对比,绘画线条的曲折伸张,诗词的赋比兴与词语的抑扬顿挫,音乐与戏曲曲调的起承转合等等,无不是阴阳之道在中国古典艺术中的体现。
第三,“太极图式”的文化模式——“生生”美学之思维模式。“天人合一”文化传统中阴阳相生的关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太极图式”。北宋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阐述了“太极”的基本特点。所谓“太极而无极”,即指太极无边无极,无所不在,它是一种阴阳相依、交感施受、互为本根的状态。“太极图式”是对于生命的产生与流行、循环往复、无始无终形态的现象描述,是中国哲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所在。这是一种特有的交互融合的艺术思维模式,中国传统艺术均表现为一种圆融的包含生命张力的形态。有学者将之视为圆形思维模式,如嫦娥奔月、敦煌飞天与汉画像之虎豹图等,其实是一种圆融而极富张力的艺术思维模式。
第四,线型的艺术特征——“生生”美学之艺术特性。中国传统艺术是一种线型的、时间的、生命的艺术,而西方古代艺术则是一种团块的、空间的、雕塑的艺术。线型艺术呈现的是一种生命的时间音乐之美,一切犹如乐音在时间中流淌,一切艺术内容都在时间中以线型呈现,化空间为时间,例如国画中的多点透视,在一幅画中展现宏大的视野,清明上河图即是。再如被称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书法艺术,毛笔是中国艺术特别是书法最重要的工具,笔势成为中国时间的生命艺术的典型代表。
四、中国传统“生生”美学的艺术呈现
宗白华曾指出,中国传统美学更多是来源于对艺术实践的总结。宗先生认为,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人应当打破过去美学只是在理论著作当中的成见,而从中国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和艺人的艺术思想中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由此,我们在研究中国“生生”美学之时,应将对艺术理论与艺术呈现的考察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从中总结概括出“生生”美学的相关范畴。“生生”美学作为中国传统的生活美学,同样也渗透于普通百姓日常的节庆活动、民间文化艺术之中,体现出中华民族对于生的期盼、祝福与感恩。
曾繁仁教授将“生生”美学的艺术形态进行了梳理,并概括出九个范畴。
第一,诗歌的“意境”。“意境”是中国传统艺术中一个最基本的美学范畴,也是“生生”美学的重要内涵,反映了“意”与“境”、“天”与“人”的相反相成与有机统一,具有生成“象外之象”“文外之韵”的生命力量。在司空图看来,“意境”即是一种“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就是透过看得见的去欣赏看不见的,最重要的是味外之旨。这正是中国“生生”美学的特殊性之所在。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以北宋宋祁的《玉楼春》为例阐释“意境”的特征。王国维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此句出自《玉楼春》上片:“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该词记述早春时节荡舟于碧波中的游春之事,然后借景抒情,以绿杨在晓寒中轻摇与红杏在枝头绽放相对,点出冬去春来、春和景明、生机跃动的景象。一个“闹”字,既写出了红杏与绿杨相对的艳丽色彩,又通过红杏之鲜艳夺目与晓来之轻寒的对比,烘托出大自然的勃勃生机。此词既充分抒发了诗人对于早春特有春景的欣赏,也体现了对大自然勃勃生机的歌颂。“闹”字写出了生命的色彩与声音,化静于动,化视觉于听觉,写出了自然的生命力量,是一种艺术的“通感”。
第二,书法之“筋血骨肉”。“筋血骨肉”是中国书法艺术特有的美学范畴,是通过书法的点线笔画与雄健笔力形成想象中的“筋血骨肉”,体现了东方传统文化中身体美学的特征。魏晋书法家卫夫人在《笔阵图》中指出:“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这里的“骨”指笔力强劲,“肉”指笔力弱而字迹粗,“筋书”指笔力劲而字迹瘦,“墨猪”是一句批评的话,指笔力柔弱、字形臃肿。所谓“血”,是要求水墨“如飞鸟惊蛇。力到自然,不可少凝滞,仍不得重改”。“筋血骨肉”彰显了中国传统艺术特有的顶天立地、骨力强劲的生命之美。
第三,古琴之“琴德”。“琴德”是中国琴艺的重要美学范畴,是传统文化对于文人顺天敬地、效仿圣贤的高尚要求。嵇康在《琴赋》中提出“愔愔琴德”之说。“琴德”,指和谐内敛、顺应自然的安和、静寂之德,要求抚琴者做到体清心远、良质美手、艺冠群艺、敬畏雅琴,以“至人”为榜样的境界。《乐记》中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这是中国文化对音乐艺术的最高要求,亦是对文人士大夫艺术修养的普适性要求,体现为一种“生生”美学的“天地”境界。
嵇康清高孤傲,不肯向权势低头,最终为司马昭所杀。他临刑前,弹奏著名的《广陵散》,曲调激昂高扬,听者无不为之动容。《广陵散》是我国十大古曲之一,据说来源于古代聂政刺韩相的故事。聂政因为感念韩国大夫严仲子的知遇之恩,孤身仗剑刺杀韩相侠累。后来,因为担心连累与自己相貌相近的姐姐,慨然自毁其面,剖腹而死。《广陵散》是激越的生命之歌,嵇康临刑弹奏此曲,使之名声大振。
第四,绘画之“气韵生动”。“气韵生动”是中国绘画的基本美学范畴,也是中国“生生”美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南朝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绘画的“六法”之说,第一即为“气韵生动”,被视为绘画的最高境界。明代唐志契《绘画微言》对“气韵生动”有精到阐发:“气韵生动与烟润不同,世人妄指烟润为生动,殊为可笑。盖气者有笔气,有墨气,有色气;而又有气势,有气度,有气机,此间即谓之韵,而生动处则又非韵之可代矣。生者生生不穷,深远难尽。动者动而不板,活泼迎人。”可见,“气韵生动”主要表现为绘画的“气势”“气度”与“气机”。有“气势”即生“韵”,“韵”是生生不穷、生机活跃、深远难尽之美。因此,“气韵生动”是一种由象征生命之力的气势形成的生命的节奏韵律,具有无穷的韵味情志和活泼感人的生命力量。
宗白华先生曾简约地概括,气韵生动就是“生命的节奏”或“有节奏的生命”。例如齐白石的《虾图》,齐老以“为万虫写照,为百鸟传神”的精神,使一个个活灵活现、充满生命力量的虾跃然纸上。画面上并没有画水,但一个个虾却俨然悠游于大江大河之中,纸上无水,留白即为水。
第五,戏曲之“虚拟表演”。中国戏曲是世界三大古代戏剧之一。中国的戏曲,以京剧为例,有两大特点,第一是亦歌亦舞,第二是虚拟表演。“虚拟表演”是中国传统戏曲的重要艺术特点,是一种虚实相生、演员与观众一体的东方戏曲模式,也是其相异于西方戏剧实景实演之处。在中国传统戏曲之中,布景、景致与空间都是虚拟的,戏曲的“环境”完全是通过演员程式化的表演表现出来的。例如,剧中的万水千山只需跑龙套者在舞台上走几步,千军万马只由一个将官和几个小兵来象征性地表演,上楼下楼只是演员端着灯模拟地走几步,如此等等,可谓“三五步万水千山,六七人千军万马”。这就是清代画论家笪重光在《画筌》中所言“实景清而空景现”。
当然,这种虚拟表演光靠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是完成不了的,它还要依靠观众的审美介入以及与演员的精神交流。有学者将这种观众的介入称作是一种“反观式审美”,即观众调动自己的艺术想象,与演员共同完成艺术的创造。这就是所谓“真景逼而神景生”。例如川剧《秋江》,表现的是道姑陈妙常乘船渡江追赶情人潘必正。舞台上只有陈妙常与老梢翁两人,全凭老梢翁的一支桨以及左右划桨的动作和二人起起伏伏、一上一下的表演,便表现出满江秋水波涛起伏的情景,甚至让观众产生晕船之感。这一切都依靠观众通过虚拟表演的“反观式审美”来完成。
第六,园林之“因借自然”。“因借”是我国园林艺术中极为重要的通过因应自然来实现自然审美的美学艺术原则。明代著名造园理论家计成在《园冶》中提出“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观点。所谓“因”,指造园时要充分因顺、借助自然环境原有地形、地势、地貌的“高下”“端正”等形态,进行适宜的创造,既要空间适宜,又要适宜于人。所谓“借”,就是借景,是突破园林所构成的空间上的内外界限,使园内园外“无拘远近”都可“得景”。因此,有远借、仰借、邻借、应时而借等。应时而借是指在春夏秋冬不同季节恰当地“借景”,既能使园林的景致丰富,更使中国园林审美不以静态观赏为主,而是在动态中多视角地融入式观赏,以动观静。这与当代西方环境美学所提倡的融入式审美相契合。例如苏州的留园,近借西园,远借虎丘山,是中国园林“借景”的典范。
第七,年画之“吉祥安康”。中国传统美学渗透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反映在节庆和民间艺术之中。年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装饰性艺术,一般是春节过年之用,发端于汉代,发展于唐代,成熟于清代。其主要内容为驱凶避邪与祈福迎祥,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元亨利贞”“四德”的美好追求。年画里的门神是驱凶辟邪的守护神,来源于神话传说《山海经》中善于捉鬼的神荼、郁垒二神,据传此二神可以捉鬼给老虎吃;后来逐渐演变为人格神秦琼、尉迟恭,以及仙道人物钟馗等,这些被人们敬畏的神或半神守卫在门,保佑着老百姓的平安吉祥。年画的另一个主题是祈福迎祥,内容包括“五子夺魁”“鲤鱼跳龙门”“年年有鱼”“福禄寿”三星、倒写的“福”字与“百子图”等。此外,年画还反映对农业丰收的祈望,诸如“牧牛图”“五谷丰登”“大庆丰年”等。中国年画的内容与中国文化对生存的歌颂与期盼密切相关,是“生生”美学在日常生活与节庆中的体现。
第八,建筑的“法天象地”。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包括宫殿宗庙、寺观庙宇、人居庭院、园林别业等,体现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相亲和的审美追求。中国传统建筑的核心观念是“法天象地”。如北京的天坛,建于明代,是历史上帝王祭祀皇天、祈求五谷丰登的场所。天坛包括“圆丘”与“祈谷”两坛,南方北圆,象征天圆地方,是一座与天地相应的建筑。
第九,汉画像之“天人感应”。汉画像是汉代艺术的典型代表,包括画像砖、画像石等。汉画像是在汉代“天人感应”观念下形成的,它以长生、升仙为主题,画面大气磅礴,五彩缤纷,表达对生命存在的热情歌颂与向往。例如马王堆的T型帛画,分天上与人间两个层次,天上的太阳、月亮、蟾蜍、玉兔、飞龙与人间贵妇人、侍从形成鲜明对比,充分反映了汉代人对现实人生的留恋,以及对理想的神仙世界、来世幸福的向往。
五、当今中国生态美学发展的新启示
中国古代以“天人合一”为其文化传统的“生生”美学的艺术呈现,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生存与审美方式。“生生”美学是一种活着的、有生命力的美学思想,已经成为当代美学,特别是生态美学建设的重要资源,并且正在与国外的现象学生态美学及环境美学进行跨文化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希望有更多的外国朋友能够理解并且逐步接受中国的“生生”美学,同时也期待更多中国学者投入到中国传统“生生”美学及其艺术呈现的研究中。这对于促进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发展,对于建设富有生命活力和中国特色的“美丽中国”,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华文化有着五千年的优良传统,是极为丰富的遗产,当前我们正面临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抓住传统文化的根和魂,秉持复兴中华文化的责任担当和热爱民族文化艺术的情怀,探寻生态美学的中国民族形态,才是当下美学学者需要探寻的一个新方向。 (整理:文学院 王涵 仇子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