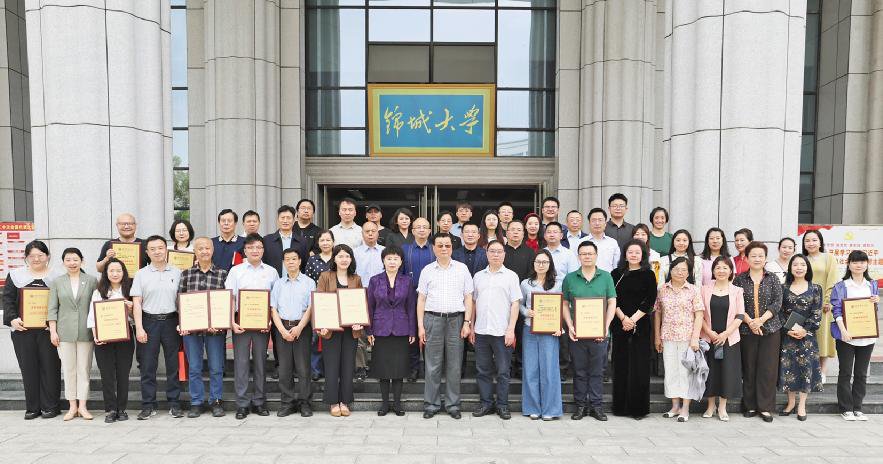十一月的此刻,是时候回顾一下我们一整年的际遇了。这个秋天,对我们的生活来说,既像是结束,也像是开始,曾因为太过靠近、太过熟稔而让我们茫然使我们迷惑的一切,现在已经变得清晰而陌生。这一年真的好漫长,感觉比前十年所有的日子叠加在一起都缓慢,都意味深长。有那么多个夜晚,我感觉我们已然山穷水尽,可当那一刻真的到来,由于置身其中,一切又变得支离破碎迷雾重重,我甚至都没能察觉那一刻的的确确到来过。
现在,我可以用一种告别前尘往事的态度来回望那些日子了,那些比任何时刻都更加真切、更加有意义的日子。但是,世上的一切都不会彻底地结束,一切的过往都不可能被永远地抛却。
那些年的日子由于岁岁相似而变得模糊不清,而记忆,有时像细筛,有时似流沙,不过我却能真真切切地记起我们到来的那一天,以及到来之后的那几个月。真真切切。就在那个三月,我们生活的根,重又扎在了那片土地上,之后的日子就像是它奇异的枝枝蔓蔓。
那一天,小山光秃秃的,落满冬日的败叶,但是果园看起来却孕育着生机一片。树木好像被红色汁液浸染得斑斑驳驳,紧致的树皮似乎已无法包裹住呼之欲出的新叶将带来的勃勃生气。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内战之后就一直属于霍德玛恩家族。不过我们到来时已经多年无人居住,当然,期间也有些佃农偶尔停留暂住过。土地虽然粗砺多石,但能给人希望。远处岩石的突出部分已经风化,颜色银白,像一颗颗裸露在风箱中的石牙,那里有我们的牧场,羊儿将在那里长得膘肥体壮。山坡上栽满了高高的果树,母亲第一天看到这一切时马上兴奋地联想到了需要收割的庄稼,需要到陡坡上采摘的苹果,不过,当时她只是淡淡地说,会有好收成的,看那些果树,虽然栽种了多年。却依然挺拔强健。“就算结了果子,也不会赚多少钱的,”我记得父亲这样说道,他顿了顿,又说,“这片地也抵押了。”
没有人搭腔,大车沿着车辙继续吱吱咯咯地行进。茉儿和我仰头看天上的松鸦,看着它们蓝色的翅膀拍打着树枝,听着它们尖锐的叫声在林间回响。榆树的枝条上挂满花蕾,棕色的枝干向天空张开了怀抱。牧场荒凉又美丽,胡桃木下淡紫色的树荫是那么整洁纯净。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那么突兀,那么让人无迹可寻。这里就是我们的土地,冰雪消融时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可是,又有丝丝的恐惧悄悄袭来———抵押,而父亲就一直沉浸在酸涩的愠怒和对未来的恐惧当中。母亲静静地坐在那里。父亲之前并没有告诉她抵押的事儿,而且,她一直以为,至少土地是不会被抵押的,土地是一切都失去之后全家最后的避难所。可是,就在这一刹那,她明白,这是一片充满不确定和变数的土地,不过,她身上固有的某种东西让她静静地接受了这一切———这种东西我那个时候不懂,可能永远都不会懂。那是一种平和,一种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平和。信念,我猜也许这就是信念吧。她承受的已经太多太多,但她从不犹疑,也不觉得凄苦。她就在那里,信念从未动摇,或者说表面上看是这样,而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知道这些就足够了。就在那个时刻,我们可以忘记父亲的话带来的犹疑和不安。那一年茉儿十岁,我十四岁,对我们来说,似乎某种更伟大的冒险已然开始。但是,父亲的目光却一直定定地落在年久失修的牲口棚上。
他,阿诺德·霍德玛恩,虽然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童年,却称不上地道的农民,而现在,他又回到了这片祖辈曾耕种过的土地。土地还是那片土地。他却没有农民该有的那种对自然的顺从———他不明白,如果时令未到,不管你是爱是恨,即便祈望得到一粒豆子,也是枉然。他十六岁就离开这片土地,在布恩的伐木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像一棵橡树或是梣树那样艰难地成长,虽然缓慢,但远比一个季节就蹿高两英尺的白杨更有价值。但是现在,这棵大树己被伐倒,只剩下树根。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多么诡异的经历———安稳平和地工作了那么多年,突然在几个月之内,一切归零,不再被社会需要,自己的价值不再得到承认,这是一种多么虚无而幽暗的感觉。多年来一点一滴努力的累积,突然之间灰飞烟灭,这一切让他也不再敢相信这片土地。
大车后面拖着我们的床。汽车和大部分家具都卖掉了。之前的生活被抛在了身后,就好像它从未存在过。过去的生活只有一部分还伴随着我们,那就是我们曾读过的书和对知识的记忆。三代人的藏书是无法被真正卖掉的,因为人类一切艰难的跋涉都已然被记载在书中。我们离开了那个邪恶的、混乱的、喧嚣的世界,来到了这片土地,虽然这里的生活依然会艰难,依然会给这个男人带来挫败感,但至少,也将会带给他回报。而这,是原来的世界无法给予的。
房子非常老旧,甚至不是用圆木,而是用木板搭建的,简陋得就像牲口棚。屋外的门廊上爬满了某种长着喇叭形叶子的植物和红色的野葡萄藤。秋天时,野葡萄黑油油的,布满井边,有一棵葡萄藤还不知被谁刻意地架在了水泵的上方。父亲在光秃秃的葡萄藤里发现了一个画眉鸟废弃的窝。他把它取了下来,这样茉儿就不会误认为这是鸟儿在春天里新筑的巢,就不会痴痴地等待那些永远都不会造访的鸟儿。茉儿在废弃的鸟窝里装满了圆石头,放在壁炉的上面,也许她以为炉火的热度会孵化出石鸟来吧———她的想法我无从知晓。她的脑子里总是装满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时她甚至显得比大她五岁的凯琳还要成熟。
第一个春天的一切都很新鲜,它在我的记忆里被切割成了两部分。有一个部分是像灰色的迷雾一样的焦虑和恐惧———父亲好像就站在这雾中。这雾并不总是清晰可见,但一直在那儿,这迷雾里还混杂着我们对这片土地的爱,这片每时每刻都会以一千种方式向我们展现它的美丽和多变的土地。记得我们到来的第二天就迎来了暴风雪,强劲的西北风从山坡上吹下来,摇晃着窗户,好像要把窗框都撕碎,拳头大的雪花敲打着窗玻璃。我们以为它是要警示我们,这里冬天会很寒冷。可奇怪的是,暴风雪过后,虽然地面上覆盖着两英尺厚的雪,大风猛烈地摇动着山核桃树和橡树,但天气却不那么寒冷。茉儿和我走到了林子里的一个石台上,那里的岩石倾斜而出,山上的流水在这里形成了小小的瀑布。我们看见了冰面下的气泡,溪水冲刷出的黑色的泥土印在冰面下蜿蜒曲折,像一只只快速游动的狡黠的蝌蚪。瀑布下面的蝲蛄浅滩上生长着蕨类植物,碧绿光鲜。阳光灼热,我俩走着走着就解开大衣的扣子,摘了帽子。回想起来,之后发生的差不多每一件事情,都像那个开始一样———在冷风和暖阳之间,不断变换又保持平衡,说不上是好还是坏,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切都胜过了原来那个世界。即便在那时,我们也能感受到,我们来到了一个充满冒险但又和谐友爱的世界,就因为它的变动不居,才让人感觉更加真实可信。它也将不受人类的干扰,以它自己的方式一直存在下去。
(本文摘自同名小说《十一月的此刻》的第一篇章《序曲,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