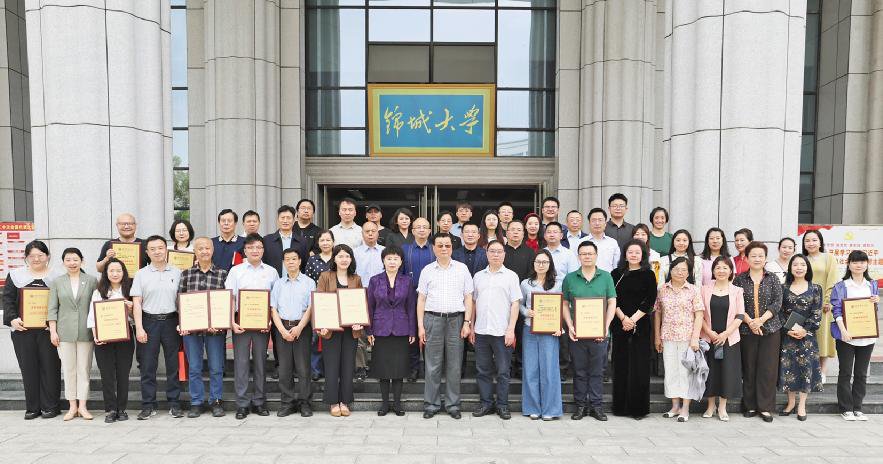枣乡的傍晚
姥姥家在著名的金丝小枣之乡———乐陵。五六岁时,我常在乐陵放肆玩闹,度过一整个夏天。出门绕一圈,凡是长着绿叶的树,树梢上总挂着枣子。有的嫩绿,有的深青,有的挂着几抹红。我最爱的还数金丝枣了。掰开半干的小枣,由果胶组成的缕缕金丝粘连于果肉之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乐陵便因它盛产的金丝枣而闻名,素有“百里枣乡”的美誉。
姥姥家是枣乡的一个小村庄,村子不大,人也不多。那片混杂着秸秆黄泥的土坯墙与泥泞小路陪伴我度过了一个个闷热又有趣的傍晚。时隔十余年再回枣乡,当年我赤脚撒欢地跑在姥姥门前那条小道上的欢愉心情,仍旧鲜活如初。姥姥家的小院不同于别家,堪称一座小型园林。门口并排着一棵枣树与一棵杏树,偌大的院子里一多半覆盖着豆角、茄子、丝瓜的秧苗藤蔓,旁边是大簇的粉白牡丹与有着细巧花瓣的金黄花儿,其繁茂程度甚至压过了蔬菜们。另一旁的小道铺满暗红色的泥砖,颇有些文艺味道。
我记忆中的傍晚,每当月光落在院子的红砖上,堂屋屋檐下澄黄的灯泡便亮了起来。灯泡功率不高,刚刚能照亮屋檐底下的小院一隅。傍晚昏暗的天色中,亮起灯的屋檐下是“逐光虫”们的大本营,“啪”地一声掉落一只壁虎是常有的事。我跟姥姥、姥爷在灯泡照亮的小院里支起方桌,摆上小木板凳,端上晚饭。桌上没什么新奇的菜,多是刚刚从院子里摘下的大圆茄子,偶尔姥爷也会做一顿拿手的黄面鸡肉。新鲜的鸡肉剁块,裹上蛋黄面糊过热油一炸,披上酥脆金黄的外壳,紧接着在热水中焯一下,葱姜蒜末一齐放入,“咕嘟”个把小时,软糯鲜香的黄面鸡便出锅了。但论起我最爱吃的,还属姥姥包的茴香大包子。我素来是不怎么爱吃茴香的,只是姥姥包的包子别有一番特色。咬一口偌大的包子,第一眼望去全是绿油油的茴香苗,但是继续往下咬,总会在不经意间咬到一块个头不小、半肥半瘦的肉片。这样的肉片在一个包子里并不算多,多者四五块,少则两三块,偷偷地埋在茴香苗里,总给吃包子的人一种探秘寻宝之感。三口五口,一个包子就在不经意间下肚了。以至于后来不在姥姥身边时,我也总挂念着这有挖宝惊喜的茴香包。每每赶上舅舅回家,总要托他向姥姥要几个包子捎回来给我吃。母亲奇怪我为何如此偏爱这茴香包,便自己买肉剁馅给我做。说来奇怪,母亲的包子里肉不比姥姥少,但却总也吃不出那番滋味。
配包子的最佳拍档自然是粥了,枣乡的粥也是独一份的。黄玉米面倒进黄河水,“咕嘟咕嘟”煮开了,便是最常见的玉米糊糊。黄河岸边一带的水质十分特殊,带着天然的泥土腥咸,让人难以下咽。但倘若碰到了玉米面,就仿佛遇到了“真命天子”,水的咸不再遭人嫌弃,反倒成了煮粥的好材料。正因为黄河水盐分高、密度大,玉米面糊得以在水中悬浮起来,在大锅熬制下煮成一碗鲜咸可口、稠稀匀实的玉米粥。
吃完饭,我跟姥爷就有的玩了。夜色里,总有我们爷俩一老一少拿着手电筒到树林里捉知了的身影。倘若实在懒得出门,我俩就坐在院儿里看星星,看着看着,姥爷张口便唱出来:“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它还是那个月亮……”我至今不知道这首歌出自哪里,但是偶尔看到星星,还是能想起这六岁时响在耳畔的歌声。我太爱这个小院子了。夏天光着脚丫踩在晒得发白的水泥门槛上,感受烫到极致的灼烧感;在院子里疯玩后跑进开着空调的屋子里,感受迎面扑来的酷爽凉意……还有我每次回枣乡时,睡的那床翠蓝色的床单,不知为什么,长大后的我每次看到它,就有一股难以名状的低落。后来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或许小时候在枣乡放肆玩闹的我,也曾在玩累的夜晚躺在这张床单上偷偷地想妈妈。
长大后离开枣乡的我,从来没同她断了联系。每年,姥姥总会让舅舅给我捎来最新鲜的大冬枣。大冬枣宛如一个小鸡蛋,鲜红的枣子一口咬下去,只听得清脆的“咔吱”一声,一股独有的清甜香气先萦绕在了鼻头上。毋需多用力,轻轻一嚼枣肉便尽数碎开来,汁水弥散在唇齿之间,枣肉细腻到没有什么纤维渣滓。嚼干了枣子的汁水,枣肉也就化没了。末了将枣核上的枣肉也吃干净,小小枣核一吐,一颗枣就进肚了。
枣香萦绕在鼻头,对枣乡的思念却时时刻刻萦绕在心头。终于有机会同母亲一起再度回到枣乡,她的傍晚依旧如十年前那样平和静谧。忙完一天的活计,姥姥、姥爷开始收拾晚饭。我与母亲悄悄溜出家门,绕到房屋后的田野闲逛。才下过雨不久,格外泥泞的田间小道一路延伸到玉米地的深处。我站在田埂的十字路口上,向四周望去,除去为数不多的几棵老枣树,就只剩下无尽的玉米茎秆。枣树叶和玉米叶沙沙作响,在傍晚的余晖中随风轻轻摆动。远远望去,一片墨绿玉米田上,浮现出一枚红油咸鸭蛋黄一般的太阳,红黄的光晕染着田野上的整片天空。老枣树们依然挺拔着,一人多高的玉米杆齐刷刷地站在田中,晚风蹭着玉米叶悄悄溜过,撞到我和母亲背后,拽起我们的衣角,接着横冲直撞地继续向前奔去,仿佛是那年在乡野间疯跑的我。
七十三岁的姥姥成了村庄里的广场舞领舞,受舞友们之托,让我帮着在网络上下载几首新式舞曲。我坐在板凳上,切换着歌曲,姥姥则在屋子里卡着节拍跳起舞来。遇到跟不上的鼓点,姥姥的舞步就像被人为设置了“二倍速”,逗得我、妈妈和姥爷大笑着仰倒在床上。傍晚吃过饭后,我跟母亲盼着去广场一睹她老人家的风采,却不想突然接到了村子一位患病已久的村民病逝的消息。姥爷匆忙放下手里的活计,赶去帮衬打理后事。大概是听说了消息,不止是枣乡,附近其他村庄的村民也都没有再像往常一样聚集到跳舞的广场上来。夜色深了,我与母亲连同几位上年纪的村民站在送丧队伍经过的路旁,看着长长的送丧队一路向北走去。
“他们去哪?”我问母亲。母亲说:“他们要去村口那棵大枣树下送魂。”“为什么?”我不解。“枣树下有神的。”母亲头也不回地答道。这个靠枣子富裕起来的村子,至今已无人再靠卖枣为生,然而最初保留下来的那份对枣树的敬畏与感恩,却历经数十年未曾变过。
枣乡在我的二十余年人生中,出现不过短短一二年。但她却实实在在地成为了盛满我美好回忆的魔盒。离开枣乡长大的这些年月里,每当走入低谷,我总不由自主地想起枣乡的傍晚,仔细回忆着小院里的一花一草,想念着夏日里鸣蝉的聒噪和门灯下蜥蜴瘦小的身影,如此,那份鲜活的欢愉心情便陡然充满了我的心间。
枣乡呵,多想永远沉溺在你傍晚的余晖中。